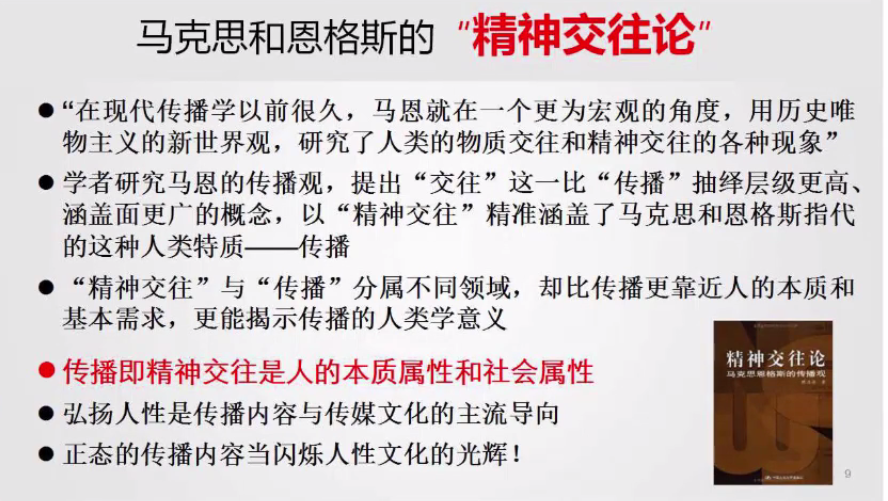
老子孔子马克思与恩格思精神交往论图解







据史书记载,孔子门徒有三千人,其中贤明有声望者七十二人(即“七十二贤”),而最最拔尖出众者只有十个人,号称“孔门十哲”。按照孔子的说法,“十哲”各有专长,其中德行以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优,言语以宰我、子贡为精,政事以冉有、子路为善,文学以子游、子夏为上。

孔门十哲图(部分)
作为圣人的孔子是位好老师,对学生从来都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很少有对学生责骂怒斥的现象,更遑论体罚。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当脾气极好的老夫子碰到顽劣不堪的学生,难免也有动气发怒、骂其为“垃圾”的时刻。这个在孔子眼中顽劣不堪的学生,便是以言语擅长的宰我。
宰我即宰予,字子我,生于鲁国,比孔子小29岁。宰我聪明伶俐、能言善辩,跟子贡一样,都是孔子非常喜欢的学生,时不时地被老夫子派到齐楚等国出使,每每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不仅如此,宰予还是一个“不唯书,不唯上”的奇才,看待问题很有自己的主见,常与孔子辩难,经常有独到的见解,但也因此屡屡触怒老师。

宰予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言语见长
孔子提倡父母死后要守制三年的做法,但宰我却认为守制一年即可,原因是“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见《论语》)”大意是说如果所有人都遵循守制三年的规矩,那么社会上很多事业便要荒废,为现实考虑,为父母守制一年即可。孔子听后大不高兴,在宰予离开后,对别的学生讲宰予毫无心肝,不配做人子。
孔子思想中的核心是“仁”,“仁”在世界上无所不在,但宰我却对此并不感冒,曾经为孔子提出一个两难问题,说假如有人欺骗仁者称井里面有仁者,那么他该不该去下井追随呢?孔子自知是圈套,只好跟他“打太极”,回复宰我说君子会去追随,却不会自己陷进去;可能会被欺骗,但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受愚弄。虽然回答得很巧妙,但属于模棱两可的答案,显得异常牵强。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见《论语•雍也篇》

宰予经常在课堂上与孔子辩难
宰我这种“不唯书,不唯上”、独立思考的精神,虽然难能可贵,但在讲究尊师重道的古代,却往往会被视为逆反之举,不免遭到老师的申斥。孔子对宰我的辩难不厌其烦,不满的情绪日积月累,终于在一件小事上对宰我猛烈“开炮”,骂他是垃圾不如的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孔子某天讲学时,发现宰我逃课,事后得知原来他在大白天睡觉。获悉真相后的孔子非常气愤,对其他的学生连发感慨,说宰我这个人就像快腐烂的木头,不值得再雕刻,又像是用粪土建成的墙面,不值得涂抹。对于这样一个冥顽不灵的人,还有什么话要讲呢?(宰予昼寝。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见《论语》)。

宰予昼寝图
古代讲话很重视用语,一般不用恶语重词,孔老夫子嘴里讲的“朽木”、“粪土之墙”在当时已达到爆粗口的程度,如果换成今天的意思,跟骂人是“垃圾”、“败类”没有区别。能让老夫子如此动怒,“孔门十哲”当中唯有宰予一人而已。
按照《史记》的记载,宰我的结局很惨,在担任齐国的临淄大夫时,因与权臣田常争权被杀,孔子听说后倍感羞耻。不过对于这个说法,为《史记》做注的唐代史学家司马贞提出质疑,他说因争权被杀的人是齐国大夫阚止,而非宰予,只因为阚止、宰予的字相同,以至于后世混淆罢了。这也算是一家之言。
说起儒家代表人物,就要先问一句怎么样才能称为儒家,或者说儒家都具备哪些特征?
儒家的特征
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十三经书为经典
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本辑大体介绍先师孔子及孔门十哲。
先师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属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出生地鲁国陬邑(今属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的学说成为中国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他兴办私学,突破官府垄断,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

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变“学在官府”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因此儒家思想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了全社会。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
2.孔门十哲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门十哲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中表现出类拔萃的十位弟子。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耕、冉雍。

颜渊,即颜回,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21年),卒于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1年),享年40岁。

他十四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

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收集在《论语》等书中,其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其为“复圣”。

闵子骞(公元前536--公元前487),名损,字子骞,汉族,春秋末期鲁国(现鱼台县大闵村)人,其先祖是鲁国的第四代国君鲁闵公,其父闵世恭为八世祖。孔子高徒,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回并称,为七十二贤人之一。

他为人所称道,主要是他的孝,作为二十四孝子之一,孔子称赞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明朝编撰的《二十四孝图》,将闵子骞孝亲的故事排在第三,使之家喻户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著名的先贤之一。

冉耕(约前544~?),字伯牛,汉族,春秋鲁国(今山东东平)人,为人端正正派,善于待人接物。在孔子弟子中,以德行与颜渊闵子骞并称。因 恶疾早逝。孔子哀叹其“亡之,命矣夫!”( 《雍也》)。官至中都宰。有“郓侯”、“东平公”、“先贤冉子”等封号。

冉雍(公元前522-?),字仲弓,出生于菏泽市冉贤集。冉耕(伯牛)之弟、冉求(子有)之异母兄,与冉耕(伯牛)、冉求(子有)皆在孔门十哲之列,世称“一门三贤”,当地人称为三冉。孔子对其有“雍也可使南面”之誉。这是孔子对其他弟子从来没有的最高评价。孔子临终时在弟子们面前夸奖他说:“……贤哉雍也,过人远也。”
言语:宰予、端木赐。

宰予(前522~前458),字子我,亦称宰我,汉族,春秋末鲁国人,孔子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宰予小孔子二十九岁,能言善辩,被孔子许为其“言语”科的高才生,排名在子贡前面。曾从孔子周游列国,游历期间常受孔子派遣,使于齐国、楚国。

宰予思想活跃,好学深思,善于提问,是孔门弟子中唯一一个敢正面对孔子学说提出异议的人。他指出孔子的“三年之丧”的制度不可取,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因此认为可改为“一年之丧”,被孔子批评为“不仁” (见《论语·阳货》)。

他还向孔子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他假设这么一种情况:如果告诉一个仁者,另一个仁者掉进井里了,他应该跳下去救还是不应该跳下去救?因为如跳下去则也是死,如不跳下去就是见死不救。孔子认为宰予提的问题不好,说:“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可欺也,不可罔也。” (《论语·雍也》)认为宰予这是在愚弄人。

宰予昼寝,被孔子形容为“朽木”和“粪土之墙”。孔子认为宰予言行不一,说自己“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并且从宰予那里改变了自己以往的不足,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论语·公冶长》)

端木赐(前520年-前44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古同子赣)。东周春秋末年卫国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受业身通”的弟子之一,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子贡在孔门十哲中以言语闻名,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之相。

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后世有人奉之为财神。子贡善货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被确为儒商始祖。

《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史记》对其评价颇高。子贡死于齐国,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政事:冉求、仲由。

冉求(前522-前489),汉族,字子有,通称“冉有”,尊称“冉子”,鲁国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县冉堌镇)人。周文王第十子冉季载的嫡裔。中国春秋末年著名学者、孔子门徒。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

前487年率左师抵抗入侵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冉求是孔子的最好的得意门生之一,在孔子的教导下逐渐向仁德靠拢,其性情也因此而逐渐完善。

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又字季路,汉族,春秋末鲁国卞(今山东省平邑县仲村镇)(原籍泗水,其后胤因避战事迁往微山县鲁桥(见济宁微山仲庙))人。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少孔子九岁,也是弟子中侍奉孔子最久者。

仲由除学六艺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他敢于对孔子提出批评,勇于改正错误,深得孔子器重。孔子称赞说:“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又说:“我的主张如果行不通,就乘木伐子到海外去。那时跟随我的怕只有仲由了。”

为《二十四孝》中为亲负米的主角。仲由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敢于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

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曾任卫蒲邑大夫、季氏家宰,是孔子“堕三都”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后为卫大夫孔悝家宰,在内讧中被杀,被砍作肉浆,孔子大恸,为之不食肉糜。
文学:子游,子夏。

言偃 (前506--前443 ),字子游,又称叔氏。 春秋时常熟人。孔门72贤弟子中唯一南方弟子。擅文学,曾任鲁国武城宰,阐扬孔子学说,用礼乐教育士民,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为孔子所称赞。孔子曾云:"吾门有偃,吾道其南。"意即我门下有了言偃,我的学说才得以在南方传播。故言偃被誉为“南方夫子”。后人配祀 孔庙,称“十哲人第九人”。

卜(bǔ)商(前507年—?),字子夏,尊称“卜子”或“卜子夏”。汉族,中国春秋末年晋国温地(今河南温县)人,一说卫国人,“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受儒教祭祀。现在,山东省巨野县有其嫡系后裔。性格阴郁,勇武,为人“好与贤己者处”。以“文学”著称,曾为莒父宰。提出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还主张做官要先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其效劳。

后来孔子丧,孔门乱,子夏到魏国西河教学。李悝、吴起都是他的弟子,魏文侯尊以为师。宋人疑之,《诗》、《春秋》等书,均是由他所授。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像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他是一位具有独创性因而颇具有异端倾向的思想家。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复兴周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因此,子夏发展出一套偏离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
《新丝绸之路》解说词之《敦煌生命》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高楼和街道也变幻了通常的形状,像在电影里……你就站在楼梯的拐角,带着某种清香的味道,有点湿乎乎的,奇怪的气息。擦身而过的时候,才知道你在哭。事情就在那时候发生了。我有个朋友牙刷,他要我相信我只是处在发情期,像图拉在非洲草原时那样,但我知道不是。你是不同的,惟一的,柔软的,干净的,天空一样的,我的明明,我怎么样才能让你明白?

忘掉她,忘掉她就可以不必再忍受,忘掉她就可以不必再痛苦。忘掉她,忘掉你没有的东西,忘掉你失去和以后不能得到的东西。忘掉仇恨,忘掉屈辱,忘掉爱情,像犀牛一样忘掉草原,像水鸟一样忘掉湖泊。像地狱里的人忘掉天堂,像截肢的人忘掉自己曾快步如飞。像落叶忘掉风,像图拉忘掉母犀牛。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
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你是甜蜜的,忧伤的,嘴唇上涂抹着新鲜的欲望,你的新鲜和你的欲望把你变得像动物一样的不可捉摸,像阳光一样无法逃避,像戏子一般的毫无廉耻,像饥饿一样冷酷无情。

《新丝绸之路》解说词之第六集《敦煌生命》
这一天是阴历四月初八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日。莫高窟大佛殿前香烟缭绕、人声鼎沸,这是中国人信佛拜佛的一大特点。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燃一炷香,每一个人都在微闭双目心中念念有词。当他们虔诚地俯首叩拜的时候,已经悄然地把自己的心愿说给了佛祖听,坚信佛会保佑他们一年平安、事事如意的。
据说四月初八祭拜佛祖是敦煌人历史悠久的传统,大概自有莫高窟起就有这一佛事活动了。因为在莫高窟的洞窟中,那些存在了上千年的佛教壁画、塑像,从来都是供人们礼拜而用的。
然而,一个特别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如此之多的朝拜人群只被允许进入大佛殿,而其他所有有壁画的洞窟却对他们关闭了窟门。这似乎不应该是传统中的禁条,那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科学技术人员,每天都要走进洞窟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跟随着他们,我们走进了莫高窟。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壁画和以往的记忆以及那些精美的画册相去甚远——它们破损严重,甚至脱落,有的后面崖体完全露出,壁画已不复存在。等等这些均被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称之为壁画的病害。
他们每天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对壁画病害进行状况调查:通过各种符号如实地把病害现状记录在案,为随后的修复与保护提供依据。
在莫高窟492个有壁画的洞窟之中,病害比例高达近50%。这恐怕就是在四月初八禁止朝会人群进入有壁画的洞窟的原因所在。而莫高窟一旦失去了作为其精神象征的壁画,就好比一个人的思想被抽空,生命就会变得苍白而无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的敦煌将如何回首往事?
自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敦煌建郡,敦煌便成为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通的门户。
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西域不稳,而敦煌恰恰成为相对安定的中间地带,一大批文人士大夫以及佛教徒开始在敦煌驻足。
公元366年,一个名叫乐僔的和尚,由东向西云游至敦煌。他在此开凿了第一座石窟,莫高窟由此创建。
应该说,是敦煌奇妙的自然地理现象感动了这位一路风尘的沙门中人:在茫茫戈壁的了无生息中,祁连山的雪水顺党河峡谷深入干渴的大漠,这条生命之链为疲惫不堪的乐僔穿起一串串希望;鸣沙山漫漫沙障,幻化无穷;三危山立石层层,有如千佛;傍晚时分,一派空灵,夕阳放射出万道金光。乐僔恍惚之中看见了佛祖在他面前显灵,于是他向着西方俯首叩拜,立志在此开窟侍佛。从此,这三危胜境成为了佛门圣地。
自乐僔开窟时间过去1600百年。莫高窟在它最辉煌的时期即唐代,已有“窟室一千余龛” 。说它是佛教圣地,名不虚传。
然而,明朝政府关闭嘉峪关后,敦煌地区的居民全部内迁,莫高窟就此在几百年当中无人管理,日渐萧条。
到1900年,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道士王圆箓与几位最不同凡响的西方探险家的交易,把全世界震惊了:前者发现了著名的藏经洞;后者用少数银两换走了这洞中大批堪称文化宝藏的佛教经卷和各类文书。敦煌莫高窟就这样又重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古人的智慧往往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姑且不论莫高窟壁画的文物价值有多高,单就古人使用泥土、白粉和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洞窟岩壁上制作壁画本身而言,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所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与保护研究所进行合作,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古人的壁画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在研究室内,技术人员仅以微量提取物通过X衍射,便可得到壁画泥层和颜料层中各物质成分及其特性;同时在特殊显微镜下,矿物质颜料的色相及其变化被准确地观察出来。 之后是实验性的复原临摹,此手法首先可使一大批画面漫漶不清的壁画重现昔日真面目,为各类研究提供基础;再则,这样的复制过程也是保护与修复壁画的重要前提。
众所周知,敦煌以及西部中国异常干燥的内陆性环境气候,是众多古代石窟壁画得以保存下来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水就成为了这些泥质壁画的第一天敌。而敦煌地区的砾石岩层中又含有较多的可溶性盐,于是水与崖体中的可溶盐的相互作用,便是引发壁画产生病害的主要原因。
为找出壁画病害的发生规律,技术人员在实验室中进行了一项壁画病害模拟试验。经过分析,他们确定出壁画地仗层即泥层的主要物质成分,分别是占六成以上的黏土,三成左右的细沙和少量的麦草,用水调制而成。其中为主的黏土,即是莫高窟前大泉河水冲刷至下游的杂质极少的沉积土,又被称作澄板土。从取材上看,特别是大量的基础材料即壁画的泥层,古人只能就地取材。而上述这三种材料正是敦煌所具备的。因此他们按照适当的比例,制作出了与莫高窟壁画泥层非常相近的地仗层模块。当模块晾干之后,用石青、石绿、铁红等几种在莫高窟壁画中最为常见的矿物质颜料,涂在模块表面,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壁画模拟试块。最后,这些试块被人为地加进了一定比例的与莫高窟崖体中性质相同的可溶盐,目的是要把它们放入试验箱中,在一个人为控制的温湿度变化周期中,观察试块发生病害的程度。
敦煌市的早晨热闹非凡,小商小贩纷纷出动,各路游客跃跃欲试。虽然今日的敦煌似乎不复丝路时代“华容所交一都会”的盛况,但它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以另一种形式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这就是旅游。每当春季来临,大客车便一辆接着一辆从各大宾馆出发,把旅游者带上那条通往莫高窟的沙漠公路。
莫高窟分南北两个区域,位于鸣沙山东麓断崖之上,总跨度1700米。石窟在崖壁上上下相接、左右比邻、状如蜂巢,最密集处上下多达五层。
据考证,莫高窟的营建是一个从4-14世纪跨度一千年的漫长过程。佛教通过石窟中的壁画在这里广为传播,同时世俗生活也被古代画师们投射到笔端。
在众多的佛陀故事画里,表现佛一人承受苦难,普度众生。其中舍身饲虎图,描绘佛的前身萨埵那太子,为救活奄奄一息的母虎与虎崽,以身饲虎的情景。在这里佛的大慈大悲,被刻画到了足以震撼人的心灵的地步。对现实生活的幻想,构成了西方净土世界的巨幅画面。其中飞速旋转的胡旋舞,在西方的乐土之上跳动着盛唐时代的脉搏。说法图中的菩萨美轮美奂,一派高贵、典雅、慈爱的尊容,传达出的是一种雍容大度的盛事情怀。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队,一路艰辛万苦,遇盗脱险、逢凶化吉,保佑他们的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这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共计45000平方米,加上2000多身塑像,集中在被称之为礼佛区的南区洞窟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壁画和彩塑一直是这里的僧侣、供养人以及民间百姓们精神寄托的对象。
与人们所熟悉的莫高窟南区洞窟相对应的北区石窟,则是当年僧侣们坐禅修行、生活起居的场所。
仔细观察这些毫无修饰、四壁皆空、矮小黑暗的北区石窟,你会感觉得出当年僧侣们的生活与南区华丽洞窟中的佛事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清静、寂寞成为石窟主人的生活基调。
据说,当年敦煌的百姓出家为僧者,人数众多。他们离开距自己并不遥远的亲人,舍弃人间烟火,遁入空门,坐进小小的石窟,修行一世,苦度一生,或许只为在莫高窟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净土吧。
所以,在莫高窟北区石窟里发现了数量相当的古代僧人的遗骨。
与此同时,在北区石窟中还出土了大量不同民族、不同文字的佛经及社会文书残片。当年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货币——波斯银币以及胡人形象的男俑,也出现在北区石窟中。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在众多文书残片中存有一份叙利亚文圣经。这说明在丝路时代,敦煌莫高窟不仅是一个佛教中心,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场所。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再没有第二个佛教石窟寺遗址,在时间跨度上和信息承载量上能与莫高窟相比拟的。因此莫高窟被今天的人们视为文化宝库,并且有着独一无二的珍贵性。
而它又非常脆弱,因为这里的壁画、彩塑都是泥质的,所以保护它就显得异常艰难。
在经过若干个温湿度循环周期后,壁画模拟试块果然发生了轻重程度不等的病害。这不仅验证了水与可溶盐对壁画的破坏作用,更重要的是为研究病害机理、找出修复材料提供了可能。
那么,所谓壁画的病害是怎样形成?又有怎样的表现形式?
据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苏伯民介绍,壁画病害的形成,简言之就是存在于洞窟崖体中的可溶盐遇水后溶解,水蒸发后再结晶,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导致结晶盐存留于壁画的泥层和颜料层中,破坏了壁画原有的物质结构。
目前莫高窟壁画的病害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起甲壁画,即壁画表面的颜料层起皮、龟裂、脱落。二是空鼓壁画,其特点是壁画的泥层与洞窟岩体失去粘结,开裂后向外鼓胀,当其无法承受自重时,就有塌毁的可能。三是酥碱壁画,主要表现为壁画整体粉化、酥松、呈糟糠状,最终彻底脱落,因此它是所有病害中最为严重也最难于治理的病害,又被称之为壁画的癌症。
科学的修复起于实验室。经过多年的试验与筛选,敦煌研究院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修复起甲壁画的粘结材料——它是一种明胶,即动物皮胶再精炼后得到的一种最接近古人作画时所使用的胶结物。因此它对壁画颜料层的副作用是最小的。它的作用即可使壁画干裂翘起的颜料层湿润后与泥层重新粘结,而又不会破坏壁画颜料层的色彩关系,即画面效果。
当对试验模块进行过无数次修复并且证明这种修复工艺有效之后,真正的洞窟实地修复方可开始。然而这毕竟是面对实物,而且是有着巨大文物价值的莫高窟壁画,因此需要修复人员不仅掌握熟练的修复技巧,也要具备相当的文化艺术素养,这样修复出来的壁画,才能达到不显山不露水、修旧如旧、画面浑然一体的效果。而这是一切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基本准则。
如果说修复起甲壁画是直观的、看得见的,那么修复空鼓壁画则是不可视、更不能立即见效果的。
修复人员首先在壁画的空鼓部位,找到一个尽可能不破坏画面效果的地方,打一个细小的孔洞,插进橡胶软管,随后灌入事先配置好的具有黏结作用的浆液至壁画的泥层与岩体之间,最终达到使岩体与壁画泥层重新粘结的目的。
这一灌浆技术是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多年合作研制出来的。这种浆液透气性好、收缩率小、强度适中、重量轻、其性质与壁画泥层非常相融。因此只要灌浆经验丰富、技术娴熟,此浆液就会很好的填充壁画的空鼓缝隙,而不致使壁画负重过多,又具有良好的粘结效果。
灌浆完毕之后,一项重要的工序就是支顶吸盐板。该吸盐板表层是一种吸附力极强的材料,在支顶空鼓壁画使其回帖的过程中,吸附浆液中的水分及其所溶解的空鼓部位的可溶盐。 最后通过局部吸盐法,彻底吸附掉残留在壁画表面的盐迹,这样就避免了灌浆后的壁画在水分蒸发时把可溶盐留在泥层或颜料层中,导致酥碱、起甲等其他病害的再发生。
关于所谓壁画的癌症,即酥碱病害的修复方法,目前敦煌研究院尚在试验中,但修复的思路仍然是脱掉壁画中的可溶盐。
从1998年至2005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对莫高窟第85窟壁画进行了历时8年的修复。它是目前世界上采用现代科技工艺修复古代石窟壁画最成功的一个范例,也是实施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一个典范。如果在未来的长时间里,这些被修复过的壁画状况良好的话,说明敦煌研究院已经找到了一整套修复壁画的科学程序。那么,尽量延长莫高窟壁画的寿命,似乎就有了可能。
1600年前,当莫高窟洞窟的岩壁上被绘制出第一幅壁画,那时的人们没有去理会画师是谁。可是当492个洞窟铺满壁画之时,后人又没能记住众多画工的名字。仅有的一些能证明画工身份的洞窟题记,现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如果这些无名画师灵魂不死的话,他们对今天所进行的壁画的保护与修复,或许会感到欣慰。 据说,创造了莫高窟壁画的古代画师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僧官,顾名思义是管理僧人的,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数不多。再就是画僧,他们是僧侣,也会作画,人数较前者略多。最后便是纯粹的画工了,他们游走四方,居无定所;在洞窟里作画,便在洞窟中起居,一旦完工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可想而知,这个巨大的绘制工程,一定令许许多多画工耗尽毕生的精力——他们走进了这状如蜂巢的石洞,恐怕就再也没有走出莫高窟。
正是这样一批优秀而伟大的无名者,为后世留下了人类辉煌的丝路文明的影像。
而这些不可移动的传世珍品,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经受着来自自然环境的各种威胁,更成为近现代人攫取的对象。
自从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于20世纪初获取大量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绢画之后,美国人华尔纳捺耐了许久,还是按捺不住了,终于来到中国。
1923年冬季,美国福格考察队在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一无所获,队长华尔纳带着对西方同行的极大怨气继续西行,目的地是敦煌。
当华尔纳于第二年初春出现在莫高窟时,他遇到的是和他的西方同行一样的情景,主持王道士外出不在莫高窟。然而华尔纳并不像斯坦因、伯希和那样期盼着进入藏经洞,因为他对藏经洞及其经卷文书兴味索然。身为艺术史家的华尔纳是带着剥离壁画的化学胶水有备而来的,因此他无须等王道士回来,便径直走入了莫高窟的洞窟之内。
一进洞窟,五光十色的巨幅壁画令华尔纳眼花缭乱,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之外,再无别的可说。”于是在王道士回来后,他同样用给银子的方法封住了他的嘴。当夜深人静之时,华尔纳用化学胶水剥离下12块在他看来堪称绝世精品的壁画。与此同时,这位识货的艺术史家还盗走了两尊彩色塑像,其中一尊盛唐时期的供养菩萨像,现已被视为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华尔纳偷偷地溜走了,他的车马队因所装宝物严重超载而显得狼狈不堪。敦煌的乡民们在得知此事后震怒了。如果说他们因缺少文化而不甚关心藏经洞文书的流失,但这莫高窟中的壁画和彩塑却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因此乡民围攻了县长和王道士,扬言要找华尔纳算账。华尔纳事后感觉到了危险无处不在,因此他第二次欲大规模剥离敦煌壁画的梦想破灭了。此后外国人欲在莫高窟的非法活动,均未得逞。
1943年的初春,第一位专职保护人来到莫高窟,他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常书鸿。
据说常书鸿和他的同事于1940年代来到莫高窟时,满眼荒凉、一无所有,唯一能栖身的地方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寺庙。他们白手起家,在这里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时间飞逝,创业者在一个甲子之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敦煌人。
如今,到敦煌莫高窟观光的游客日渐增多。人们惬意地行走在被修复了的古栈道之上,精美的壁画使人流连忘返。然而这种景象与敦煌研究院历史纪念馆的一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里,常书鸿等人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堪称老古董的生活资料,从一个侧面注释着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的开篇史。如果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脑海中生成一幅幅活的影像,你也许能够深刻体味在这大漠之中迈出第一步的创业者的生命意义。
春夏之交,敦煌在一天内下了一场超过年平均降水量40毫米的所谓的大雨。这对敦煌人的生活而言再好不过了,对莫高窟就未必是好事了。
看到莫高窟的崖面被雨水阴湿的部位,凭直觉便可以感到这对洞窟里的壁画是绝没有好处的。
一个平日里是供上香人烧香而用的大缸,此时盛满了雨水,倒影晃动,俨然把莫高窟映成了一幅水彩画。相信游人会觉得这别有一番情趣,然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人员想必是不希望这种景象过多地出现。
春雨过后,是永无休止的风沙——严重时能见度只有几米远。
风沙的破坏力不言而喻,尤其是莫高窟及其壁画在沙暴的侵蚀下,异常脆弱。早在1940年代常书鸿等人接管莫高窟时,就因为它长期无人管理,洞窟和壁画被风沙掩埋磨损者甚多。
看来无论让敦煌人期盼的雨水,还是令人生畏的风沙,对于莫高窟而言,就像无形的杀手,侵蚀着每一幅壁画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对莫高窟及其壁画的研究与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60年的时间里,敦煌研究院几代人为此费尽了心血:从早期的单一临摹和抢救性加固,到如今使用先进的科学工艺方法修复壁画、治理环境。他们走过的是一段艰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历程。用心急如焚为子求医的母亲和悉心体察及时施药的大夫来比喻这几代人对莫高窟的用心,绝不为过。
沿着敦煌的母亲河党河向上游追溯,一直可以到达祁连山。
自古以来,每当春天降临,祁连山的积雪都会融化流入党河。干渴了一冬的党河便开始复苏,它带着生命的活力顺着大漠流向敦煌,于是绿洲里的生活又充满了生机。
似乎是要顺应天时,就在早春时节,敦煌的一户农家新添了一个小生命。此时恰逢小生命过百天之际,主人家要做很多很多的饭菜,以供前来道喜的乡亲们享用。
女主人的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因为这是他们家四代同堂了,这孩子便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所有的敦煌人以至中国人都会有相同的喜悦和企盼,因为生命的延续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同样,莫高窟也是有生命的。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莫高窟的壁画、彩塑铺展开来,可以在沙漠之中布成一个长达二三十公里的大画廊。而这个画廊便承载着莫高窟的生命——即敦煌的文化生命。
如何更好地延续这个生命,不仅是那些正在莫高窟努力工作的人们的使命,它也将成为全人类一个共同的课题。
